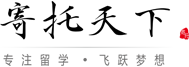| 寄托天下 | 2014-12-02 14:32 | 浏览3744次 |

关于作者:袁应笑,1989年生,浙江金华人。2011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,2013年耶鲁硕士,目前于伯克利读博。
十三年前,我从镇上的小学到城里的初中。那时我羸弱,瘦小,带着小地方的孤僻与自卑。我的同桌是个皮肤很白、个子很高、脾气也很孤傲的男生。他有个很好听的名字,叫做明亮。
可是他很讨厌我。
时间隔得太远,我也不记得我是哪里得罪了他。他故意把他的课桌与我的课桌拉出一段距离。好粗好宽的一道三八线。能不和我说话,他就不和我说话。
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。然后关系慢慢改善。是因为什么改变,我也不记得。也许是因为我冲他的侧影傻笑,也许是因为我借作业给他抄。反正,他的课桌和我的课桌越来越近,直到最后,并在一起。
然后有一天,班里的小混混来找我挑衅。具体为的什么我记不清,总之把我惹哭。明亮霍地一下跳出来,提拳就打。一个打三个,威风凛凛。
他赢得正得意,班主任老师进来,一看,气得不行。
这不是他第一次在班里打架。但绝对是最后一次。
被叫到全班面前,一边打手心一边骂。响得简直全校都听得见。
十三年前,体罚在我们那儿,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老师拿着自备的竹板打手心,一下一下,清脆响亮,像屋外白晃晃的阳光。
打完以后让他站着墙根拿手掌打墙。
“很喜欢打是不是?你打啊,打啊!让你打!”
全班肃静,鸦雀无声。就听见他一下一下打墙。
我胆颤心惊地坐在座位上,一声不敢吭。我没有举手跟老师说,老师你别罚他,他是因为我才跟别人打架。
第二天他没来上课。第三天他父母来办转学。
他转学是对的。
那时我们都不懂上网。QQ还没有普及,电邮还没有踪影。我们没有手机,也没留电话。那时我们东西不多,回忆不多,牵挂不多。一背书包,就各自回家。一经离别,就各自天涯。
太快了,太快了。还没有好好说上一句什么,还没有好好给你一个拥抱,我们就这样散了。
后来有了校内,有了微博。我在无数个社交网站上搜他的名字:“明亮”。一堆的结果,可就是没有他。
以至我怀疑,那个孤傲的高个子男孩,是不是我的一个梦境。
他现在在哪里呢。是在漂泊,还是已经有家。是不是已经长大。是不是已经有了他的她。
十三年。我已渐渐模糊了他的模样。我光记得他有个耀眼的名字,叫做明亮。
我大学毕业,在北京工作一年。那一年憋屈不得意,就像挤在军博那个小小的十平的房间。可是现在回想,那又是我许久来最快乐的一年。因着有他。
也是皮肤很白的大个子。脾气很好很温柔。
我们的单位离得很近。我在复兴门,他在五棵松。每逢周末,我们就挤着可怕的一号线,鹊桥相会。
我们在一起规划未来。想着怎么在北京郊外买房子生孩子。他见过我爸妈。我们几乎要谈婚论嫁。
请原谅我略过我们在一起的所有。因为每一个细节,好像都连着我泪腺。
我想我们真的是彼此相爱。可是印象里,我们好像从来没有说“我爱你”、“我也爱你”。
唯独在黑暗里,我们眼睛对着眼睛。
闪闪发光的。
说爱你,难道是这样见不得光也见不得人的事情。
中国人不可以像美国人那样,把love you挂在嘴边,挂在邮件末尾,挂在电话筒上。中国人要用成十成百的勇气,要用漫长漫长的时光去酝酿。
好不容易等酝酿好了,可是却没有时间了。
古汉语有情没有爱。爱这个字,是吝啬的意思。所以会这样吝啬说。
后来我下定决心出国读书。
他出奇地冷静。
他说他在考ACCA,说不定可以去美国工作。他说他也可以申请美国的学校,说不定可以去同一个城市。他说,只要想在一起就一定可以在一起的。他说了这个又说了那个,说到最后,他的眼泪滴在我脸上。他哭着对我说:“你不走真的不可以吗?你可不可以不走?可不可以不走啊?”
我真的从来没见过,也没想过,一个高高大大的男人可以哭成这个样子。还是被我弄哭。
我果然是个很坏很坏的女人。
我十分悲观地想,每一次相拥相聚的温暖,是不是都是为了离别更悲伤。
后来我又想,也许根本就不会像当初想的那样难。不过是十个小时的飞机。也许是我们爱得不够努力,敌不过十个小时的飞机。
可是等我到美国后,他的QQ头像再也没有亮,人人账号删除。原来我们的交集,确实就这一点点而已。可以删除。
以后我回北京。我已经没有勇气再拨他的号码。
你好我也不开心。你不好我也不开心。所以电话打了也是白打。
我还有他的微信号。可是我要跟他说什么呢?过得还好吗?工作还好吗?还挤在单位宿舍吗?有新女朋友了吗?要结婚了吗?
还是跟他说:我还爱着你。
我的最初和最后的恋情。
无声的错过和无声的我爱你。
每个人的故事写出来,都会是一部太长的小说。可都支离破碎。因为有太多离别。
他们说真正相爱过,就做不成朋友。所以我们注定要离别,要陌路,要天涯。
可是终成正果的呢。终成正果的,就可以逃过别离吗。
我外公去世。
外公是很沉默的人,到过年都说不了几句话。他去世前生病,整天说着胡话,像把一辈子没说的话都攒在了最后一年。只是说胡话也就罢了。他还唱戏,发疯,把屎尿甩在外婆脸上,把外婆赶出家门。外婆任劳任怨,尽心尽力地照顾他。如此磨了大半年。大家都想,真是个解脱。
我们那里的葬礼要哭号,要叫喊。一堆儿女跪在父亲灵前,轮着哭叫,越响越好。
外婆该是哭丧的主角。她应该哭得最响最凶,可是她没有声音。
她就坐在那儿,木头雕出来似的。没有声音也没有眼泪的。
我看着外婆那样,心想,如果最后是这样的离别,是不是不如当初就不聚。
有一天外婆寄宿在我家。凌晨醒来,发现外婆呆呆站在窗口。妈妈起身去看她。她忽然来了一句,说:“要不,我还是跟他去吧。”我妈骂:“你神经!”
是不是因为人太脆弱,所以才需要爱的韧劲,将人生捆缚成一个因果。
《致青春》里女生跟男生表白,说:“我喜欢你。”男生答:“……神经病!”
是不是爱情,就是我们突然脑抽发神经。
***
忽然写这样一篇文章,是因为听了一个日本文化讲座,叫作《“我爱你”及其他》。讲座的大意是说,日本人不说“我爱你”。“愛してる”这个句子,只有在电视里才会遇见。
男生想要对女生说爱你,就会指着天上的月亮,说:“月亮真漂亮,是吧?”(きれいな月だね),或者说:“我真喜欢你的眼睛。”(きみのめがしきなんだ。)
女生想要对男生说爱你,就会说:“我喜欢你这个方面。”(あなたのそういうところが好きなの。)
丈夫想要对妻子说爱你,就会说:“妈妈做的料理真好吃。爸爸真幸福呀。”(母さんの作る料理はうまいねえ。父さんは幸せだよ。)
妻子想要对丈夫说爱你,就会说:“你真温柔。跟你结婚,我真幸运!”(あなたってホント優しい。結婚してよかった。)
老师接着举了一个说出“我爱你”的例子。可是在葬礼。
2014年6月29日的产经新闻,标题『 ダンカン絶叫「初美-!!愛してます!!」 』(邓肯绝叫“初美——!!我爱你!!”)。
邓肯是日本喜剧演员,本名飯塚実。她的妻子在6月22日因乳癌过世,享年47岁。28日东京中野区成愿寺的告别式,邓肯在四百人面前号泣。新闻里这样描述他的哭号:
「もしかしたら初めて本名で呼ぶかもしれないけど…」と前置きしながら、「初美-!! 飯塚初美-!! 僕は初美を一生!! いや、永遠に!! 地球が無くなっても愛してます!!」と叫んだ。
(“也许这是第一次我叫你真正的名字……初美——!!饭塚初美——!!我爱你一生一世!!不,我永远爱你!!我爱你直到地球消失!!”)
我羡慕他。我羡慕他有资格也有机会,可以当着全世界的面,大声说出我爱你。
我们一辈子发神经。
© 版权信息:本文为作者授权寄托天下发布,如需转载请注明原作者、来源和原文链接。
- 相关阅读
- 寄托热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