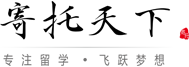| 寄托天下 | 2014-10-16 09:41 | 我要评论 | 浏览3336次 |
关于作者:Fiona__Zhao@weibo |The only obligation to which in advance we may hold a novel is that it be interesting.
Lake Ontario
总觉得来到加拿大,只是换个地方,做自己一直在做的事情。加拿大很美,拍出的照片满目的蓝,湖水,瀑布,第一眼的惊叹与感动以至泪眼朦胧,估计此生都不会忘怀。
Thousand Islands
小镇也好看,独立的小屋,屋前缤纷各异的花园。和墨尔本很像,那种街边种着紫盈盈熏衣草的记忆片段,倘若重生。只是墨尔本虽大为城,街道是比这儿宽些,却相对是静的。这里来往车辆纷杂,甚至到了深夜,还时常会有车嚣张地吹着哨子疾驰而过。
生活亦是平淡却舒心的。超市里的果蔬,吃得乐不可支。稍想偷懒,煮袋泡面,顺道扔进半颗西兰花,吃完胃里竟翻滚起来,舌尖酸涩。原来我的胃也被调教得乖巧娇气了。
Homemade Lunch
至于住,除了和室友的作息时差将近五小时以外(错,自然在我),一切还是可喜的。随时可以冲蒸腾的热水澡,打开冰箱就有冰镇果蔬和酸奶,床虽简单,但床垫仍是柔软的。大书桌前一张矮沙发,盘腿而坐,看书、看电影,都是极其奢侈的身体享受。室外零下二十几度的冰雪天地,室内一件短袖,冷了加件针织衫,就过冬了。
A Room with a View
至于旅行,我还在摸索自己的脾性。为了新鲜感,哪儿都想去。善变耍赖的个性,临行前常常从心理乃至生理全方位叛变。小时候被爸妈拖曳着走过不少地方,近一点的绍兴婺源,远一点的云南海南;上大学机缘巧合,陆续踩了一些地方,辛辣的四川,好到不能再好的英伦;之后性子越发野起来,瞒着家里去西塘、内蒙,后来日本去不得,对不起好友,只能去北京。父亲电话来的第一句:“你不会在日本吧?”原来父亲看我,一直看得如此真切。
依照两次身在国外的经历(高中稚嫩无知的那次不算),细细想来,估计是这样的:只有身在国外,才会晓得国内旅行的便捷;只有身在国外,当旅行变得不可或缺,才会萌动起回国也要多走走的渴念;也只有身在国外,才会明白有朋友同行是修来的福分,独自一人上路,则是苦痛却成长的修行。
Christmas Parade
孤单。在美留学四年多的挚友被问及在国外最大的困难,她说:“孤单。一个人的时间很多。总要找点事情干。比如健身。”这次出来前,人生历练丰富的朋友也说:“出国生活,很苦逼的呀,寂寞。”在这里读书的学妹问我:“你在复旦平时都做什么呢?我在这里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做。”当我的脑子里旋转起和志同道合、相处得欢到不能再欢的好友胡吃海喝、天南地北胡扯的画面,我才知道,原来在国内读书的自己,那么幸福。
但是说实在的,回到文章开头,在这里,我虽时常胸口堵塞,但隐约觉得自己还没有陷入过于孤单的境地。自己作息古怪,和国内的时差基本在可忽略的范围。朋友,只要我投降主动发消息,通常都会立马回的,尽管有时在字里行间读出不耐烦的情绪,也会闷到坐在公车看窗外都会一股冲动涌上来,非要强硬地,才能压回势要决堤的泪。
Inflamed Leaves
这就是我在加拿大大致的生活。关于去国外交流的“重点”,则是下面这部分了。(这绝不是经验贴,只是我个人的经历,之所以写,一来是自私的想法,希望能总结一下交流的生活;二来也想与可能感兴趣的朋友分享,把自己看到的,拿出来给没有看到的人瞧一瞧,说不定可以为他人省却一些弯路。)
先说一下我的大致情况,以备读者参考。我在复旦读了一年药学,大二转入英文系,大三去英国交流一学期。毕业后继续在复旦读英语文学专业。研一下基本在出版社实习,偶尔做笔译和口译。关于未来:大二时想做口译,大三交流后想出国读文学,大四直研后觉得没有未来了,研一实习后想做编辑。是,我很善变。那我现在的想法又是什么呢?我和朋友说,不做口译,不做学术(这两者我都体验过了,决定已不再是天真的冲动),能做文学编辑就做文学编辑,不行就去高中当英语老师,再不行,随便了。闲暇时,若是有机会做文学翻译,最好;不行,读书,写文,足矣。
这次的交流,至少帮助我更加肯定了以上的想法,当然,也有很惊讶的发现。来到这里之后,我才真正知道学术是什么样。比如,老师称呼底下的学生为fellow colleagues,比如别人看到你在读Wodehouse就会问你是在消遣吗(因为和课程无关),比如老师对期末论文的定义是你不要想着写完就能回家过圣诞节,你要想着把这篇文章投到journal之后可以发表。
Queen's University
女王的硕士和博士一道上课。这学期的建议是选两门课,另外再上两门类似于“职业培训”的课,一门教你如何做TA批改作业组织tutorial,一门请已在别的大学获得任教资格的校友回来做经验讲座。
以上这些事实一开始让我非常吃惊。原来职业性如此强。我选的课上,一半是博士,一半是硕士。我发现博士和硕士还是有差别的,比如博士真的知道很多,他们的发言不很频繁,但都很有分量,援引的知识通常需要名词解释。而硕士会相对活跃,天马行空,批判性与思辨性极强。博士基本未来已定,就是当professor,硕士分为两类,一类也是心意已决,另一类则是抱着试一试看一看的心态,对未来还是茫然的。
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话痨,在英国交流时,课堂上的我非常活跃,但是在这里,也顶多算“宜动宜静”。到了这个阶段的人,说实话,都非常聪明(我不算),所以,如果你要做学术,肯定也会变得非常聪明,天天和非常聪明的人在一起。这是好的一面。但是也有另一面,那就是你真的需要脚踏实地地阅读,写论文,建立原创性的观点,并捍卫它,最后,发表。publish or perish,真的不是传说。关于竞争性,研究生阶段的seminar已不容小觑,曾有professor将之形容为intellectuals "publicly wanking off"。
Library at Queen's
对于文学专业呢,还想多说一点。那时在英国交流,学得很开心,小的community,和professor非常熟,总是没事就去他们办公室和他们聊天,那时我很担心自己的英语毕竟不能和英美国家的人比,而且文学于我,也是后来才爱上的,读得太少太少。不知是不是那边的老师太nice,他们总是说我可以,没问题。现在读了研究生,我又出来了,现在我自己的结论是,就英文来说,可能是没什么太大问题。但是,我确实没能做到当时英国老师说的国外文学研究生的招生条件:你要对每个时期每种文体的英语文学都有涉猎。也就是well-read。与其说我不想读,不适合,还不如说,我真的没能力读。这不是小时候爸爸数落我的畏难情绪,这是事实。另外,课上真的都是白人,除了我以外。如果你well-read,想来读,也先做好心理准备,可能你是唯一的“非白人”。
- 相关阅读
- 寄托热选